梁照亮講於2011年11月12日星期六晚 萬佛城大殿 A talk given by Liang Zhao Liang on November 12 (Saturday), 2011 at Buddha Hall of CTTB
Audio clip: Adobe Flash Player (version 9 or above) is required to play this audio clip.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here. You also need to have JavaScript enabled in your browser.
 諸佛菩薩、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佛友、善知識:阿彌陀佛!上次聽近柔師給我們分享,講法的時候,提到師父以前訓練我們說法,是不准我們帶小抄,而要當場看到有什麼樣子的機緣,就從內心講出來。那我也試著今天也這樣子講講看。雖然這個是第一次,實在有一點緊張。所以假如有講得不太如法的地方,請各位法師跟善知識多多指導、指正。
諸佛菩薩、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佛友、善知識:阿彌陀佛!上次聽近柔師給我們分享,講法的時候,提到師父以前訓練我們說法,是不准我們帶小抄,而要當場看到有什麼樣子的機緣,就從內心講出來。那我也試著今天也這樣子講講看。雖然這個是第一次,實在有一點緊張。所以假如有講得不太如法的地方,請各位法師跟善知識多多指導、指正。
我是要講有關師父的一些的事情,因為我覺得在當時,我們沒有特別地珍惜。可是這一回回到聖城,碰到很多佛友,還有法師,並沒有機會可以見到師父。我的感覺就說,在我當時,十八、九年前,在聖城住的這段時間裡,聽到師父的一些給我們講的法,還有看到的一些經歷,我覺得值得在這邊跟大家分享。
有一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,就是漢堡大學來聖城參觀的這件事。
耐法師今天早上給我一本雜誌,上面寫著說,羅哲思神父在師父圓寂的時候,在萬佛殿裡面舉行彌撒的儀式來紀念他。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提起的事,因為當時在一九九三年時,漢堡大學學生來聖城,做他們的短期修學的時間,我們當時在場,師父也提到,給我們介紹過羅哲思這位神父。
在當時,師父就邀請羅哲思神父,就是第二天早上,讓他來舉行望彌撒的儀式。我現在不是很記得是幾點,可能是早上六點鐘吧,還是怎樣子的一個情形;現在想起來,覺得當時沒有把握機會去參與是很可惜的。
因為我是覺得很難去想像,有其他的宗教的神職人員,比方說天主教的神父,或基督教的牧師,他們會把他們的教堂讓出來,借給佛教的法師,來舉行大悲懺,或其他的一些佛教的宗教儀式。為什麼這個是很重要的呢?因為其實對師父來說,他的胸襟是很廣大的,他甚至不覺得說佛教本身是一個宗教,而是一種智慧。
所以師父都是用他的親身實際的行為,來切切實實地說到做到,他想要教我們的這些道理。所以感覺上,那時候羅哲思神父,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地欣賞師父的這一點作風。他在那個雜誌上面,也提到這點。
有一件事情,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蠻有趣的,那是跟恒實法師有關。我覺得那個是在大眾發生,在這邊分享應該是蠻有意思,而且那個事情,也可以點出師父他的這種教導弟子的嚴苛及一絲不苟,就是說,非常非常地,對我們來說很受用的地方。
我想他(實法師)應該還記得, 即使他不記得,至少我們觀眾席裡面的,記得是相當清楚的。當時漢堡大學來的其實不是很多的學生,差不多十來個,不像現在的規模。在座談的時候呢,上面坐了一兩個法師;現在我不是很記得其他人,可是我知道,恒實法師是坐在上面的。
所以會議一開始的時候,師父就走進來。然後他在上面的講員跟下面的聽眾學生之間。也就是說他剛好是坐在恒實法師的前頭,不過他是側面坐的,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側面。
(有一個學生進來,在觀眾席上。)有一個在觀眾席的學生,舉手問說--因為他看過恒實法師的三步一拜,認出恒實法師--他就說,「哦,你是不是就是那個三步一拜的那個法師?」恒實法師就微笑一下,點了一下頭。就是這樣子。
結果,就是這個輕微的動作。師父馬上頭就轉過去,就看他一下下而已;非常短,實法師的頭就垂下來了。
當時我的感覺就好像是看電影那種電光石火這樣子,我看到,原來這些都不用話講的,直接就讓恒實法師說,不能有那樣子的貢高的心,或是歡喜被人家認出來,很高興的那種心理。
因為看到這樣的情況,我印象非常地深。當時我的一個想法就是,誒,其實被人家認出來,或者說做了一個蠻開心的事情,被人家注意到, 不也是人之常情,稍微開心一點,這個好像也無可厚非的這種感覺。
但是,因為師父這樣子的教化,我就馬上知道,哦,沒有,事實上對修行人來說,你的起心動念太重要了,一點點的那種,片刻的懈怠,或是一點點的自滿都不行。就是像在三昧水懺裡面的悟達國師,他其實坐在沉香寶座上一剎那,也是這樣子的一個小小的自滿,或是貢高,他的冤親債主就找上了。
在當時,我的很深刻的一個感覺就是,我一直在想,對於一些佛教裡面的高僧大德的這些故事,或者是棒喝,或者是教化,我們好像都只在《高僧傳》,或是《傳燈錄》這一類的書籍上面看到。但是對我而言,在當時就是活生生在面前上演的一幕像拍電影的這樣子。
也是因為這樣子,那種珍惜的心會起來。就是說,師父是時時刻刻都在教化我們的,不論用什麼樣子的方式。而且也因為這樣子,我覺得有那樣的機會可以恭聆聖誨,可以把這樣子親身的經歷,在這邊和大家分享,結法緣,我也覺得是很榮幸的一件事。
另外一件事情呢,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。那是在一九八七年左右,當時大概是剛到聖城沒有太久。那時候我還沒有常住,是在學校念書的時候。當時師父其實都還會用他的拐杖打人家的頭來加持的時候。
當時我是帶我媽媽一起過來。就是大概在中間方丈坐的地方,師父在坐著,大家就圍著,讓他一個一個(打),有的時候不見得打得到。
那次--我其實都已經忘記是什麼法會,反正我們後來就是開始圍進去--我是一直都覺得怪怪的,好像要擠在前面,很怕落在後面的樣子。所以大部份--我現在想起來--大部份的時候就是一些居士, 特別是有小孩子的,他們就會一直希望往前擠,擠個位子給孩子這種情形。
我記得,那個時候實在是很擠,我實在很不願意去,結果媽媽就一直把我往前推這樣子。我可能也覺得我已經太大了,不適合在那邊跟人家擠。所以,其實我那個時候跪的地方蠻遠的,有一點點掙扎。可是我媽媽就把我往前推,叫我趕快上去啊!
我一方面當然也希望,媽媽不要很失望,假如我沒有被「打」到。可是又覺得,實在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在前面搶。 後來看到旁邊有個小男孩要擠上前去, 我記得我回過頭, 想跟媽媽說,:「沒關係,讓他一下。」我就記得我才剛退了一步而已,師父的那個棍子(拐杖)就打到了。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有點奇特,因為我離師父其實還有點遠的。
那個棒大概打得太重,所以我到現在,每次只要想到問自己是不是不爭,我就常會想到這件事情。有時候就想到,哦,其實當時我也不過是一點點的念頭,讓別人一下而已,師父就知道了。
因為我看好像還有一些時間,所以我再講一個小小的故事。就是當時,可能大家也知道,師父給我們上對聯課,還有訓練我們怎麼樣講法。對聯課呢,其實我當時因為也在女校跟男校教書,所以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可以參加。另外好像當時已經一九九三年左右,師父的身體狀況也不是特別好。所以他回到聖城的時間也沒有很長,通常一個月大概兩三次吧。
但是,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,當時我住在 cottage二號,他(師父)住在三號;他只要回來,我們看到燈,就知道他回來了。
但是,其實多半幾乎都是不用看到燈就知道師父回來,因為好像聖城的氣氛就很不一樣,感覺大家有時候會比較緊張,謹慎,在準備東西。或者有時就是只是很雀躍,很歡喜那樣的心情。
有一次,我記得,就是我突然之間就被叫上要翻譯,幫師父翻譯。我從來就沒有做過,也不曉得怎樣做,坐在師父旁邊的時候,就開始非常地緊張。我坐在師父旁邊,等到他講得差不多,其實我可能有在抄筆記吧!後來師父就看著觀眾席就講,「果普!怎麼舊的人都沒有翻呢」,之類的。後來恒賢法師就上來了,坐在我旁邊,我整個心就安定下來。
為什麼我會很緊張?主要就是,因為翻譯師父的講法,好像一個字都不能漏掉;要不然好像就覺得大家那種,「啊,師父講了什麼,你沒有翻到」 (雖然沒說出來,但會感覺到大家那種很迫切, 很渴望的心情),這樣子會有很大的壓力。今天就分享這些,阿彌陀佛。

 我為什麼會盡量想把上人的法寶傳到中國呢?因為這是上人的遺願。上人對我們說要把正法帶回中國,我當時也不明白。可是到了1995年,那個時候的中國已經慢慢開放,寺廟都可以讓人去參觀,可以讓人去拜拜。寺廟裏也有出家人,可是那些出家人都好像上班一樣,早上九點鐘去上班,下午五點鐘下班。後來我發現,原來很多根本不是真正的出家眾,只不過是上班族,他們領的是政府的錢。所以後來才明白,上人為什麼說要把正法帶回中國。就是因為中國雖然有很多寺廟,但真正的佛法根本就沒有。
我為什麼會盡量想把上人的法寶傳到中國呢?因為這是上人的遺願。上人對我們說要把正法帶回中國,我當時也不明白。可是到了1995年,那個時候的中國已經慢慢開放,寺廟都可以讓人去參觀,可以讓人去拜拜。寺廟裏也有出家人,可是那些出家人都好像上班一樣,早上九點鐘去上班,下午五點鐘下班。後來我發現,原來很多根本不是真正的出家眾,只不過是上班族,他們領的是政府的錢。所以後來才明白,上人為什麼說要把正法帶回中國。就是因為中國雖然有很多寺廟,但真正的佛法根本就沒有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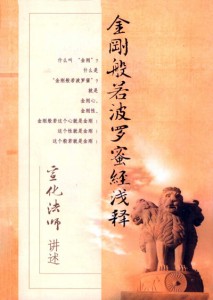 有今天的成果,我不敢居功,這都是恆雲法師、恆瓏法師、恆鸞法師、近果師等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的一番辛勞而成的。如果沒有他們的支助,沒有他們的勞苦,我們無法把上人的法寶變成可以在中國出版流通的經書。除了中國是簡體字,我們這邊都是正體字外,還要配合中國種種的法條規章才得以出版上人的經書。根據萬佛城的知客師告訴我,今年很多從中國來萬佛城拜訪的大陸居士,大都是因為看到上人在中國流通的法寶而知道萬佛城,進而敬仰上人而來的。在中國播下上人的教法種子到今天總算有看到一點點的成果。
有今天的成果,我不敢居功,這都是恆雲法師、恆瓏法師、恆鸞法師、近果師等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的一番辛勞而成的。如果沒有他們的支助,沒有他們的勞苦,我們無法把上人的法寶變成可以在中國出版流通的經書。除了中國是簡體字,我們這邊都是正體字外,還要配合中國種種的法條規章才得以出版上人的經書。根據萬佛城的知客師告訴我,今年很多從中國來萬佛城拜訪的大陸居士,大都是因為看到上人在中國流通的法寶而知道萬佛城,進而敬仰上人而來的。在中國播下上人的教法種子到今天總算有看到一點點的成果。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,上人在小的時候是很貧困的。但是上人也很刻苦,他從來沒有因為他家裡的貧困,而不努力上進。雖然上人只上學兩年半,但是他自己很努力的自修,很努力的學習,所以上人對四書五經、醫、卜、星、相沒有一樣不通,沒有一樣不懂。也因為這個原因,他希望在這個世界上,任何一個沒辦法、沒機會讀書的人,都能夠有機會、有資金去上學,因此他希望要辦教育。因為上人這個願力,加上一些熱心人士的捐助,所以我們就在中國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會。
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,上人在小的時候是很貧困的。但是上人也很刻苦,他從來沒有因為他家裡的貧困,而不努力上進。雖然上人只上學兩年半,但是他自己很努力的自修,很努力的學習,所以上人對四書五經、醫、卜、星、相沒有一樣不通,沒有一樣不懂。也因為這個原因,他希望在這個世界上,任何一個沒辦法、沒機會讀書的人,都能夠有機會、有資金去上學,因此他希望要辦教育。因為上人這個願力,加上一些熱心人士的捐助,所以我們就在中國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會。 這一次,近果師、近順師和我一起到了中國很多貧困的地區去做了探訪。其中有一位學生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動,她現在已經大學三年級了。但是當他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,他家裡突然發生了不幸的事故。首先是他爸爸得了癌症,不幸去世了。接著他媽媽因為照顧爸爸太勞累,也摔斷了骨頭,成了殘疾。因為這樣,他們家裡的收入突然間有變化了。這個大學生在讀一年級的時候,就覺得是世界末日了,她可能沒有機會再去上學唸書了。後來經過老師、朋友的推薦,知道有我們這個教育基金會,因此她就向我們申請,也得到我們基金會的資助,因此她懷著非常感恩的心情給我們寫了一封信。寫得非常令人感動,因為她說假如沒有這個機會拿到宣化上人的教育基金,她可能就沒有機會再繼續上學,可以唸到現在大學三年級。
這一次,近果師、近順師和我一起到了中國很多貧困的地區去做了探訪。其中有一位學生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動,她現在已經大學三年級了。但是當他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,他家裡突然發生了不幸的事故。首先是他爸爸得了癌症,不幸去世了。接著他媽媽因為照顧爸爸太勞累,也摔斷了骨頭,成了殘疾。因為這樣,他們家裡的收入突然間有變化了。這個大學生在讀一年級的時候,就覺得是世界末日了,她可能沒有機會再去上學唸書了。後來經過老師、朋友的推薦,知道有我們這個教育基金會,因此她就向我們申請,也得到我們基金會的資助,因此她懷著非常感恩的心情給我們寫了一封信。寫得非常令人感動,因為她說假如沒有這個機會拿到宣化上人的教育基金,她可能就沒有機會再繼續上學,可以唸到現在大學三年級。
 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阿彌陀佛!今天晚上輪到近燈上臺學習講法。個人離開聖城已經兩年,法師很慈悲,派我到華嚴精舍去學習,對我而言華嚴精舍是一個學校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華嚴精舍,但是我這一次回來看到很多新的面孔,也許有人沒去過,所以用今天晚上的機會,作一個簡單的報告,和我在這兩年得到的經驗。
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阿彌陀佛!今天晚上輪到近燈上臺學習講法。個人離開聖城已經兩年,法師很慈悲,派我到華嚴精舍去學習,對我而言華嚴精舍是一個學校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華嚴精舍,但是我這一次回來看到很多新的面孔,也許有人沒去過,所以用今天晚上的機會,作一個簡單的報告,和我在這兩年得到的經驗。 關於華嚴精舍平常辦的法會,每個月有地藏法會、楞嚴咒法會、拜懺法會(拜藥師懺或水懺)、念佛法會;這些就是每個月固定的法會。當然也有特別的法會,就是觀音法會、彌陀法會、華嚴法會……等等。特別在華嚴法會,每天誦經是3個小時。從早上7點到10點, 是為了方便上班的信徒來參加,念完經後才去上班。但是星期天,還是保持我們固定的法會。所以每天在3個小時內,誦念4卷到5卷《華嚴經》,長的就是4卷,短的就是5卷。
關於華嚴精舍平常辦的法會,每個月有地藏法會、楞嚴咒法會、拜懺法會(拜藥師懺或水懺)、念佛法會;這些就是每個月固定的法會。當然也有特別的法會,就是觀音法會、彌陀法會、華嚴法會……等等。特別在華嚴法會,每天誦經是3個小時。從早上7點到10點, 是為了方便上班的信徒來參加,念完經後才去上班。但是星期天,還是保持我們固定的法會。所以每天在3個小時內,誦念4卷到5卷《華嚴經》,長的就是4卷,短的就是5卷。 早幾個月,我們討論墮胎的問題,哦!大家對這題目很有興趣。上個月我們講到離婚的問題,當時也強調上人的看法,就是說,「一個人離婚多少次,到臨終的時候,他的靈魂就分開多少次,來生就會墮到畜生道。」
早幾個月,我們討論墮胎的問題,哦!大家對這題目很有興趣。上個月我們講到離婚的問題,當時也強調上人的看法,就是說,「一個人離婚多少次,到臨終的時候,他的靈魂就分開多少次,來生就會墮到畜生道。」 這些孩子都是很喜歡講話,年紀從12歲到17、18歲左右,平常講個不停的,但是那一天吃飯,哦!都沒有出聲音。我們建議學生們要珍惜食物,不要浪費可吃的東西,他們寧願起來幾次拿食物也不肯丟掉它。老師和家長們看到學生們的行為,哦!很高興,所以今年他們又來了。今年來這一批有80位以上,年齡從11歲到18、19歲。我們也在網站上做了一個報導,如果有人喜歡,可以去看看今年學生們來參訪我們精舍的過程。
這些孩子都是很喜歡講話,年紀從12歲到17、18歲左右,平常講個不停的,但是那一天吃飯,哦!都沒有出聲音。我們建議學生們要珍惜食物,不要浪費可吃的東西,他們寧願起來幾次拿食物也不肯丟掉它。老師和家長們看到學生們的行為,哦!很高興,所以今年他們又來了。今年來這一批有80位以上,年齡從11歲到18、19歲。我們也在網站上做了一個報導,如果有人喜歡,可以去看看今年學生們來參訪我們精舍的過程。 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我叫做魏果時。《大寶積經》裡頭有個菩薩;佛說這個菩薩因為有這四種事情,會造成他退失菩提心。OK!時間的關係,我只能說把我知道的淺顯地講一下,細節請自己去體會,也許在網絡或是在哪裡都有這些經典,很容易看到。這個《大寶積經》,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說:大乘佛法的這個法寶都在這裡了,都積在這一部經典裡,所以叫做《大寶積經》,基本上經名的意思來源是這樣子的。
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我叫做魏果時。《大寶積經》裡頭有個菩薩;佛說這個菩薩因為有這四種事情,會造成他退失菩提心。OK!時間的關係,我只能說把我知道的淺顯地講一下,細節請自己去體會,也許在網絡或是在哪裡都有這些經典,很容易看到。這個《大寶積經》,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說:大乘佛法的這個法寶都在這裡了,都積在這一部經典裡,所以叫做《大寶積經》,基本上經名的意思來源是這樣子的。
 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我叫做魏果時。剛剛講說,對這個《六祖壇經》有什麼心得,個人想講一點我自己的一些很淺見的心得。當然,有講錯了或者是不圓滿的地方,請大家不用客氣指正;不用怕給我沒面子,沒關係的,就直接講了,看我動不動氣。
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我叫做魏果時。剛剛講說,對這個《六祖壇經》有什麼心得,個人想講一點我自己的一些很淺見的心得。當然,有講錯了或者是不圓滿的地方,請大家不用客氣指正;不用怕給我沒面子,沒關係的,就直接講了,看我動不動氣。 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今晚輪到沙彌親光練習講法,若有不妥,敬請指教。今晚是以聖人的慈悲與教育為主題。
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今晚輪到沙彌親光練習講法,若有不妥,敬請指教。今晚是以聖人的慈悲與教育為主題。 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佛友:今天輪到近中結法緣。如果講到不圓滿的地方,請包容。
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佛友:今天輪到近中結法緣。如果講到不圓滿的地方,請包容。 我想,我們可以在此地安住修行,這因為宣公上人的德行。上人的願景,是將佛法帶到西方,而現在正是時候,我們何樂而不為呢?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機會,融入這個團體。
我想,我們可以在此地安住修行,這因為宣公上人的德行。上人的願景,是將佛法帶到西方,而現在正是時候,我們何樂而不為呢?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機會,融入這個團體。 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晚上好!阿彌陀佛!我是黃素梅,法名親觀,今天晚上上來跟大家學習結法緣,如果有講得不如法的地方,敬請諸位慈悲指正。
諸佛菩薩、宣公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:晚上好!阿彌陀佛!我是黃素梅,法名親觀,今天晚上上來跟大家學習結法緣,如果有講得不如法的地方,敬請諸位慈悲指正。 1992年是我第一次到萬佛聖城,在萬佛城住了五個月,很幸運碰到了第一個敬老節,那時上人提倡敬老懷少。我聽到上人是這樣講的,上人說:「每一年在秋天,天氣不冷也不熱時來舉辦敬老節。」為什麼要舉辦敬老節?除了對長者表示關心照顧之外,因為在萬佛聖城有中、小學,所以上人是用一個很有智慧的方便法門來設立敬老節,讓學校的學生有實踐對長輩的尊敬,或是孝道的機會,因此創辦了敬老節。
1992年是我第一次到萬佛聖城,在萬佛城住了五個月,很幸運碰到了第一個敬老節,那時上人提倡敬老懷少。我聽到上人是這樣講的,上人說:「每一年在秋天,天氣不冷也不熱時來舉辦敬老節。」為什麼要舉辦敬老節?除了對長者表示關心照顧之外,因為在萬佛聖城有中、小學,所以上人是用一個很有智慧的方便法門來設立敬老節,讓學校的學生有實踐對長輩的尊敬,或是孝道的機會,因此創辦了敬老節。
